10月21日,影视人类学年会会议专题三的主题为“跨境和海外影像民族志:实践与方法”。跨境影像民族志方法与实践单元,由复旦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主持。

云南大学张海老师以“冲突、困境与宗教信仰——缅甸科钦难民离散影像记录”为题,分享了在冲突困境中缅边境克钦难民的影像记录,关注点涵盖难民生存空间,地理空间、文化空间、情感空间,提出是否能够帮助到当地人的困惑,带出社会担当的问题。离散影像记录关注战乱的前后2011到2015年不同阶段,从行为上的一种流离失所到心理上的疏离。
中国传媒大学王宁彤老师通过 “流动的记忆——老挝一个跨境庙村的离散、变迁与文化认同”的报告,结合《花山》、《魂归何处》的拍摄实践,提到“个体性”与“完整性”的问题, 通过影片当中的个体在仪式当中和节日中的活动,来呈现节日的深层结构,如世俗的体系问题,权利结构问题、经济问题,亲属问题、族群记忆问题等等,并分享了拍摄中的“平视和互视”关系。
罗红光老师、富晓星进行了细致点评。罗红光老师认为:比较典型的影视人类学的这种尝试,值得一提的有两点:一个是跨境,五十年代大调查时,搞民族识别四个指标里的空间也意味着文化有一个边界,特别强调的文化的一种本质,但实际王宁彤的片子(所呈现的内容)也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拍法和对话,这是拿摄像机本身的一个权利,通过影片可以发现,首先客观上呈现了不同文化,但在文化上有共同祖先、共同的信仰,在时间和空间被割裂以后,实际上很多东西是叠加的,在文化认同方面值得注意。

富晓星老师认为:结合政治核社会的因素再来看的话,这个问题更加复杂,尤其他还涉及到流动,涉及到中国、老挝,而且回到老挝之后又涉及到从美国回来的,因此实际上呈现的是一个混合体的状态与一种矛盾性。包括他跟不同的人群之间、再社会化、融入,他们之间的信任、沟通,也有复杂的情绪,但是复杂的情绪在节日志这样一个脉络下,或者说一个喜庆的节日下,能否以一种非常好的力道把他表现出来,是一个主要问题。在涉及关于拍摄与被拍摄人的关系时,她提到:权利是否是平等、是否是平视,通过何种方式展现,这种认知的转变、或自我反观是否体现在影片中,以何种可能方式体现等问题。
罗红光老师认为:张海的片子也是一种流变的文化认同的研究,但是在特殊的战争背景下做的,他有一个社会担当,这种动意对于人类学者而言,可能是有一种号召力的。他提出:“我们应该向他学习,就是你哪怕是搞环保的,或者搞什么教育都可以,或者研究志愿者也行,就是对人类学的那种知识如何还原给社会,当然他可能还在琢磨用什么方式。”

云南大学寸炫老师以“家庭Ÿ国家Ÿ记忆——缅甸和顺华侨口述历史研究”为题,分享了缅甸和顺华侨口述史的经历,从文化认同、人物细节、重复讲述、国家历史背后的平民史观等角度做了分享。
纳日碧力戈老师做了点评:“中国的复杂共同体就是从像你们研究的那些,充满个性和张力的个体里看,中国的复杂性,而不是简单的看一个市场经济,看房屋是涨了还是没涨,那就比较明显,最复杂的地方就在边缘,你们多看一下边缘,多看一些个性,因为人类学本来就是做个性的。”
李德君老师的发言题目是:“为什么拍摄《龙潭佤乡》”。他分享了跨国拍摄佤邦的经历,佤邦是一个外界涉足甚少、却又迫切希望了解之地,也是一个正在发生变化,传统依然生动之地,是缅甸的第二特区、武装割据区、鸦片烟种植区,也是一个贩毒的通道和重要地区,情况非常复杂,他讲述了很重要的体会:“第一不要先入为主,感觉在里面接触到的都是非常详和的气氛,不是凶险的,不要带着外界的眼光,要自己去看是什么东西。第二点感受是民间传统文化的顽强生产力,民间文化像这个复杂情况一样,一个是全民皆兵天天打仗,但是民间文化依然在顽强的生产。” 他认为: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拥有顽强的生产和生长的力量,这样的力量不可侵犯。
纳日碧力戈做了点评:“想跨界首先要考虑界从何来。本来就是佤族的人,一夜之间变了,边界没了,回到人类学的老话题,各种边界不会一致,因为人是活的、是流动的,人会学习,基因也会流动,所以说我们从老先生的这里边看到实事求是,人类学是最实事求是的一门学问。”

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庞涛发言题目为:“影像志方法进入日常生活的路径,兼谈喜马拉雅山地与都柳江流域影像民族项目”,强调文化并置是人类学常用的比较方法,以实际拍摄实践讲述它是通过画面的组接、通过生活场景的组接实现叙事,是影像在进行文化描写的时候独有的一些优势。“以《河畔的鼓声》开始,后面所有的影片都用的表现方式,都是在并置的条件下做的,我们关注的这些并置的话题,不是话题了,就是日常生活中关注的点是日常话题中的共同话语。”日常讲述虽然不太呈现这种并置,但是也是发现问题的路径,认为影像志运用到日常生活,是语境中的日常生活是看待文化的一个角度,希望从日常生活中介入到传统的民族志的领域。
罗红光、富晓星老师做了细致点评。罗红光老师认为:“寸老师的发言,讲口述史用一个说自己家族里面的一个案例,可能从人类学在国内人类学使用家族作为研究对象,应该是在信任程度上比较高。因为这话语他本身就是文化,如果资料足够的话,能够支持关于国家文化认同的这样一个研究。”他提出:“影片其中几个故事有机的整体在哪里?是我们研究人员用我们的话语给他建构,还是通过他们的话语、他们的系统,让他们来形成一个文化的景观?如果那样,我觉得这个片子一定是完整的,论文也是。”他认为:人类学有足够的时间、智慧处理这样的问题,在足够长的时段的口述史资料的前提下,词频分析是一个手段。可以通过这两种方法,一个是词频分析,另一个就是通过集体意识的方法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。
关于李德君老师的案例,罗老师认为他采用的是比较经典的人类学方法,强调人类学的人文关怀也是一个亮点:“我把我的视角、视觉换了个立场,用一个内部的视角再来看他们自己的时候,发现并不是像人们想的全是枪火、政变,实际他们的生活很详和,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很危险,我觉得他的发现是让我们换了一个立场以后,呈现出了一种文化。但是李老师讲的那个很好玩的地方是:他通过一种用镜头的方式介入,然后也跟他们打成一片,他(才)具有这样的结论,如果是过路客,也拍像记者一样的,你肯定得不出这个结论。”
罗老师认为:庞老师对方法学的思考,一直贯穿在自己的研究和拍摄里面,是一直特别享受拍学者电影。像情景剧这种,在懂文化的情况下是可以这样安排的。他认为在呈现真实的问题上,是用一套确实能够控制的一套方法来进行描述的,比如到了3D时代,同样一滴水滴往下滴,角度、深浅各异,人类学用自己的方法观察的时候,因方法、客观性已经在变,所以客观性是人造的。因此在呈现这个客观性上首先承认“我们是用了一套方法更加贴近真实。”
最后罗老师提出:“有什么样的办法去把我们学的、从对方那儿获得的人类学的知识再还原给社会”?人类学家有一个社会担当需要注意,并建议影视人类学和国图联手,如果把影像的音频、视频、图片,尤其这三类成果,数字化之后有合作,互惠互利,然后扩大到中国的“一带一路”战略,也是对社会的一个担当。
富晓星老师就不同的发言者做了点评,提出离散影像可能是危机影像的一个结果、影像的互惠与回馈、“结构化的乡愁和碎片化的主体”等内容。
“张海老师说的离散影像,连同前面两位老师提的灾难,王老师提的的911,庞涛老师提的天灾人祸,与利比亚的危机影像这个本身是有关联的,首先它有自己主体的声音,同时去除西方想象中的一种污名化。离散影像很可能是危机影像的一个结果,但是他同时又是扩大的另外一个问题的过程,这里面如果我们说危机影像里面提到很恐惧,是对死亡的恐惧,那在张海老师这个更长的过程性疗伤的过程中,是一种对故原的依恋,如果危机影像是对死亡的绝望,那么张海老师影像中呈现的是对回家的绝望。那么对回家的绝望里面,这里面联系到王宁彤老师,她有回家的欣喜。但是认为两位老师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,就说当你们回到流入地的时候,首先面临的是生存,或者在离散时的家中,而这个问题在寸炫老师的口述史里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解决,所以我觉得这三者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。
当我们做跨国拍摄或者对异文化观察的时候,自己带有一个想象,能否破除这种想象的瘴气或者魔障,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问题。
其三是提到的帮助和解决,我觉得罗红光老师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有一个探索,我们人类学在谈如何去回馈、帮助社会, 目前我看到的影像是您是在客观呈现这个行动项目,换句话说您是在远远的观察,那这个是您要一直持有的态度吗?此外换句话说您的影像能不能独立于您记录的,或者说您阐释的可以做另一番介入,我觉得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,但是我本身更期待您的影像也会做出,像罗红光老师一样的一种帮助,或者是一种互惠和回馈,这是我对张海老师演讲的一些看法,然后我觉得影像表现力非常好,我很喜欢,那个影像也很感动。
寸炫老师的演讲我觉得是:结构化的乡愁和碎片化的主体,结构化的乡愁提到了从中国到缅甸,然后您又追溯到清朝又包括建国以后,这些都是政治上制度上的东西,是我们改变不了是僵化的,所以是结构化的乡愁,碎片化的主体。她建议:在丰富个人细节以及在个案的选举上, 在某几个个案上,从我们人类学的方法,比如这种定性的研究,他的个案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关注,主要对同一个事件重合的力量, 这个本身对一个事件的不同态度的反应,反倒会让个案更加丰满和整体。”
对李德君老师的实践经验,富老师做了回应:“首先一定要实践,首先是你拿到什么样的材料,再去讲述什么样的故事,赋予什么样的理论。此外有一点提到非常好,就是民间文化的韧性。当我们呈现一个社会变迁或者空间流动或者离散之后,同样面临着变迁,那变迁就是像刚才提的同根同源,面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如何延续,因为他不断的在流散,如何做一些适应性的生存,这种民间文化以一种变体,或新的形式进行保存或者进行转化,本身也是特别有意思的话题。”
对于庞涛的发言,富老师认为:“综合他这几十年关于影视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,真的是既有全局又有细节,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思考。”她梳理了四个方面,来理解文化并置:一种是影像语言的语法的并置,通过平行、交叉剪辑来实现,第二个是内容的并置,更多的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,包括不同的群体、个体,包括能动的个体在里面起到的作用,以及一些人类学观察的一些因素,实际上还是一直提到的人类学的整体论,、文化的全貌观。第三,在结构的并置中提到的是具体的总和概念,每一个场景都是大的文化场景的一部分, 最后构成了文化的全貌。第四,是一个策略的并置,这里面也提到了我们最近的人类学的感知性观念,比如由熟转生,比如一些非常化的场景,发生意外、破坏日常、能动性的个体,或者像我总爱做一些实验性的东西,但是这些一些看似对田野破坏的异常的事件,如果我们对日常生活有敏感性,或者有长期的观察,以及理论的经验化,我们会回到最初他一定会走到日常,而为日常呈现一个更加丰富的面貌。”
纳日碧力戈老师做了点评:“田野这样的词,不是静悄悄的,要关注当地老百姓的关键词,当地老百姓如何分类。首先要关注当地老百姓的关键词,当地老百姓如何分类,他的分类系统和我们不一样,所以说这个分类词系统很重要。
比如同样是树木在他的分类系统中,树木一定和萨满和那些神仙这些在一起的,我们说树木的时候,所以说关键词和分类系统很重要,像咱们说的这个树木的时候,看那个树就想给他伐了,伐了做木头实木的那个价值高,人家看那个树木不是,比如说孙曾田拍的片子一开始国外弄一个萨满,那个树木不能随便砍的,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那我们就爱护森林了,同样在萨满的那儿调查研究,他说你不用跟我们讲分类自然,那个自然在我们的分类系统就是妈妈,我们能不爱护妈妈吗?这个关键词就很好。同样我们说个人的时候,说个体英文是individual,这个词是divide,这个不能再分了,后来他们做研究的时候,发现这个词跟英文表述不一样,在那个地方他是用颗粒来分的,人和万物都是用颗粒联系在一起,不存在英语说的individual,不存在这样的分类,所以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,万物有灵,为什么把这个山叫做爸爸,把那个树叫做哥哥,用我们的词我们不能理解,在人家的词汇里就可以理解了,所以这个很重要。第二个是我想所谓的客观,客观他一定和合谋,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一起,是各种各样客观,各种各样的一个综合,形成所谓的客观,所以纯粹客观我老实说是没有的,但是他一定是合谋,这样就需要把图像的影片,和最抽象的要加到一起,所以我是一直做三元不做二元,所谓的二元他是一个脑子里、心里的,所以现在整个社会科学都在转向,又要回归到物质性,回到肉身性等等的翻演,这个是一个大趋势,但是不能走偏了回到完全物质性,那不行,我们主观投入那个神秘主义是非常重要的,一定要保护神秘主义,人要留一些神秘。”
在庞涛主持的“海外影像民族志方法与实践单元”中,浙江大学阮云星教授就“影视人类学研究与非洲书写探新:晚近日本学界动态与启示”,梳理了关于日本影视人类学晚近的动态。邓启耀老师在点评中提到数字化之后的分享机制。郭净老师介绍了中日之间在记录影像之间的交流方面的历史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影视人类学室雷亮中做了题为“海外中国形象的影像建构:非洲中资企业影像志之实践”,结合2015年拍摄实践应用型影片案例,讲述在中国走出去的战略、海外投资过程中与海外中国形象带来的一些问题,从中国人的角度如何从影视人类学角度介入做民族影片,完成海外中国形象的影像建构。希望影片希望是一种宽容化的理解,促进他们对事物的一个理解,以一个企业的影像志反射出来他们当地人怎么看他们的,他们自身怎么来看这个问题。

郭净、李德君、王宁彤就人类学与海外中国形象建构展开讨论,提出需要更多国际人类学的田野,在民族关系、国际关系等方面,人类学尚有很大空间可以拓展。郭净老师希望大家把眼光完全从欧美收回来一部分,回到亚洲,这是日本的学者的观点,日本如此,中国也如此,回到亚洲来再去关注周边的印度、日本、韩国这些周边的国家和我们的历史关系、影像的关系,会发现非常多的东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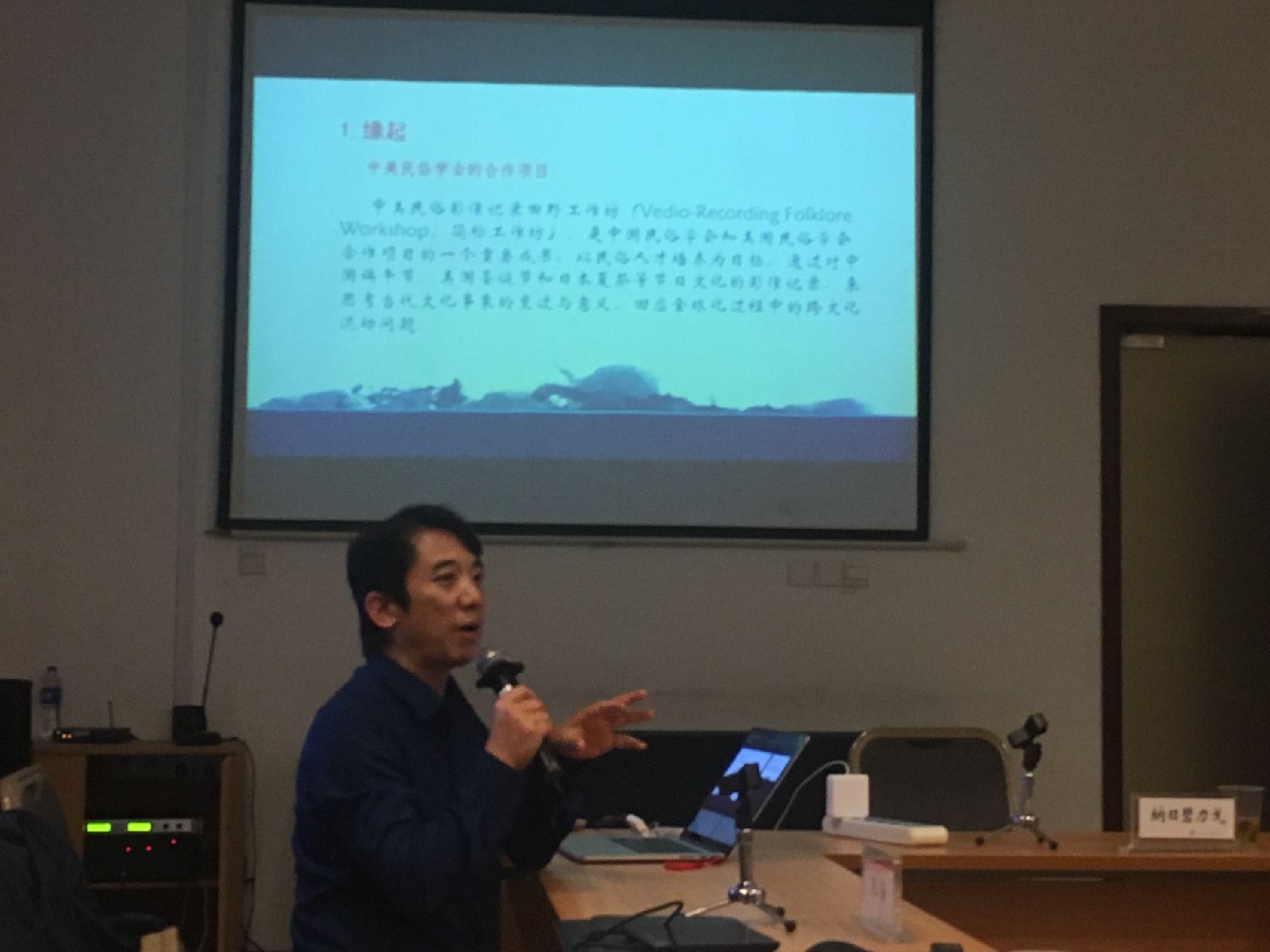
华中师范大学孙正国教授论述了“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的可能性”,通过工作坊的拍摄实践,对美国的节日、中国的节日、日本的节日这文化的影像记录,来思考当代文化变迁的意义,回应全球化过程当中汉文化流动的问题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杜世伟老师报告题目为:《环北极圈地区驯鹿文化的碎片化与整体性—基于中国、蒙古国、俄联邦跨境民族的驯鹿文化考察》,结合2016年国际合作项目的拍摄实践中国同俄罗斯的驯鹿群体的调研项目。淮阴师范柳邦坤教授以“一带一路背景下人类纪录片民族文化传播的创新策略”为题,以黑龙江的鄂伦春族为例讨论推介、传播鄂伦春民族文化。郭净、纳日碧力戈、李德君老师做了点评,王宁彤、孙正国、哈布尔、卢芳芳等参与讨论。
在“专题三跨境和海外影像民族志”会议的讨论与总结环节,由纳日碧力戈老师做了会议总结:首先,从时空交融到流动的面孔,人类学研究感情也有一段历史,国家也好老百姓也好,都希望美美与共,万象共生,学问同情感捆绑在一起。第二、研究跨界民族与影视人类学是不谋而合、互相关联,都是一个过渡带的研究、研究模糊性,这是研究中国亚洲复杂性的一个重点,也是解开中国亚洲之迷的一把钥匙。第三、做真学问,不能脱离物感物觉。